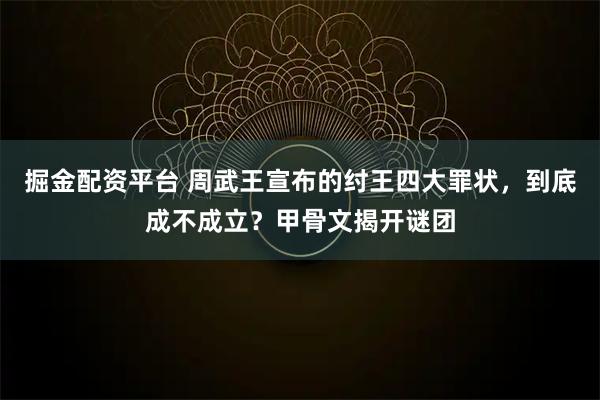
关于商纣王的罪状,最可信的记载来自《尚书》,因为它是最接近商纣王时代的文献。相比之下,战国、汉代和晋朝的记载可信度较低,因此我们更应关注《尚书》中的内容。但《尚书》里的两篇记载——《牧誓》和《泰誓》——有很大的差异,《泰誓》中的罪状显然不可信。
《泰誓》中记载了许多纣王的罪行,比如“焚炙忠良,刳剔孕妇,斮朝涉之胫,剖贤人之心”,还提到“狎侮五常”。其中“五常”指的是儒家的五种美德: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这些概念出现在汉代董仲舒的学说中,而周武王的时代并没有这些明确的概念。因此,周武王不可能说出“五常”之类的话,这使得《泰誓》里的纣王罪状显得不真实。
相比之下,《牧誓》提供的罪状要可信得多。在《牧誓》中,周武王在出征前对纣王进行了批判,列举了四大罪状:“纣王听信妇人之言、昏弃祭祀、昏弃贵族兄弟、重用逃亡罪人”。这些罪状看似明确,但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它们是否成立。
展开剩余64%首先,关于“听信妇人之言”。虽然中国古代普遍存在“男尊女卑”的思想,但在商代,妇女的地位实际上非常高。商朝有许多女性拥有重要地位,最著名的如妇好,她是商王武丁的妃子,曾多次指挥军事行动,担任祭祀活动的重要角色,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和封地。从考古发现来看,商代的女性在社会中有很高的参与度,甚至可以上战场。因此,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,在商代并不算什么特别的罪状,反而可能是社会常态。周朝的女性地位较低,因此他们可能认为纣王这样做是一种过错。
其次,关于“昏弃祭祀”。商朝的祭祀活动非常重要,商王一直与神权(祭祀者)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。商王武乙曾通过“射天”压制神权,商代的帝王往往努力寻求摆脱神权的控制。纣王也不可能放弃祭祀活动,因为这样会削弱自己的权威。周武王以此指责纣王,显然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辩护,而不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实。
再者,关于“昏弃兄弟”等罪状。商朝的继承制度在纣王之前经历过多次变动,尤其是“兄终弟及”的传承方式。在这种制度下,王位的继承并不总是通过父子继承,而是兄弟之间的传递。纣王的行为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,避免外部势力干扰。因此,他未必有意抛弃兄弟,而是更注重通过父子继承来确保政权稳定。
最后,关于“重用逃亡罪人”。商朝末期,许多贵族阶层与纣王不和,这可能导致纣王倾向于提拔那些地位较低、没有复杂背景的人。比如他重用了许多出身贫寒的人,甚至包括战俘或奴隶。在商朝,提拔不拘一格的“小臣”是有传统的,这样的做法本身并不见得错,反而可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。而周武王批评纣王这点,其实忽视了商朝社会的背景和传统。
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,周武王列举的罪状大多是站不住脚的。历史的胜利者往往会通过这些罪状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,而纣王被后人描绘为“失民心”的暴君,实则是胜利者为自己争取民众支持的手段。实际上,如果站在商朝的角度来看,纣王并未犯下那些所谓的罪行,周武王的批评更像是对他进行污蔑和指责。
发布于:天津市盛鹏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